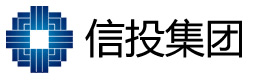今天是
民法典研读笔记:股东会与董事的权力之争(四)
本文转自公众号“迷思的忒弥斯” 作者 蒋保鹏
(4)剩余权力归属说。公司法或公司章程对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划分的规定不可能包罗万象,总会出现未能涵盖的特殊事项,由此形成所谓公司治理的剩余权力,如果此项剩余权力归属股东会是为股东会中心,如果归属董事会,则为董事会中心。钱玉林教授在《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评价》中指出,剩余权力是公司治理和权力分配中出现的一个不确定权力空间,在这个空间,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分别拥有多大的权限,没有一个定量,而是一个变量,可变因素在于章程的规定,而章程属于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因此,在这个变量中,完全由股东大会掌握主动权。为了达到平衡,在立法上的基本反应,就是将这些可变的权限暂定为董事会的权限,但不具有专属的性质,股东大会可通过章程予以保留,从而剥夺董事会的这些权限。如日本、韩国公司法上的新股发行权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种论证方法,很容易让人想到私法上的“法无禁止则允许”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法律这种强制力的规范之外,人所享有的私权不受限制。因为民法是以人作为主体和目的的,即康德所主张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那么“法无禁止则允许”的原则是在这种把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基本认识上的逻辑顺延,反过来也可以佐证把人作为法律关系中心的基础判断。照此而言,做一下对比,我们可以说,上述的剩余权力的归属,也就决定了股东会还是董事会作为公司机构的核心地位。所以这种学说的说服力还是非常强的,可以较好的用于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中心的界定和判断。
但是也可以看到,按照公司立法的基本设计,公司治理中的绝大多数权力都是经过长久实践、反复梳理提炼并被类型化之后进行法定分配的,完全被立法遗漏、游离于公司法条和公司章程之外的公司事项已无许多,剩余权力并无太大的空间。而且,这些被遗漏的公司事项,无论从其与公司和股东利益关联与影响的程度还是就其实际发生的频度而言,一般都远逊于法律和章程明定的公司事项,对这些事项享有的剩余权力无论进行怎样的分配,都不太容易实质改变公司明定权力分配已经形成的治理格局,仅以少数无关紧要的剩余权力归董事会行使便认定为董事会中心主义似乎也有不妥。也就是说,以剩余权力归属来判断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和权力争夺,在立法和实践尚不完善的时候较有意义,但随着立法的严谨和科学化,以及实践经验的丰富,这一标准的意义在逐渐下降。当然在某些领域,例如公司重大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等问题上,无论是立法还是章程,都可能存在模糊不清的地带,这就会产生解释的问题,即解释权归属于股东会还是董事会。要注意的是,某些交易行为,从层级上看,可能并不属于法律或章程规定的重大事项,但数额可能相当可观,对公司可能产生重大影响,那么究竟是归入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范围内,还是第四十六条?
还有一个问题,剩余权力归属的观点,在特殊情形下的确具有界定公司治理中心的特殊意义,即当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处于主次不清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中心非常模糊时,剩余权力的追加极有可能打破既有的权力均衡,足以凸显或奠定 股东会或董事会的治理中心地位。因此,剩余权力的观点,在判断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和权力分配、争夺上,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的加强条件。
(未完待续)
(4)剩余权力归属说。公司法或公司章程对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划分的规定不可能包罗万象,总会出现未能涵盖的特殊事项,由此形成所谓公司治理的剩余权力,如果此项剩余权力归属股东会是为股东会中心,如果归属董事会,则为董事会中心。钱玉林教授在《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评价》中指出,剩余权力是公司治理和权力分配中出现的一个不确定权力空间,在这个空间,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分别拥有多大的权限,没有一个定量,而是一个变量,可变因素在于章程的规定,而章程属于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因此,在这个变量中,完全由股东大会掌握主动权。为了达到平衡,在立法上的基本反应,就是将这些可变的权限暂定为董事会的权限,但不具有专属的性质,股东大会可通过章程予以保留,从而剥夺董事会的这些权限。如日本、韩国公司法上的新股发行权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种论证方法,很容易让人想到私法上的“法无禁止则允许”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法律这种强制力的规范之外,人所享有的私权不受限制。因为民法是以人作为主体和目的的,即康德所主张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那么“法无禁止则允许”的原则是在这种把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基本认识上的逻辑顺延,反过来也可以佐证把人作为法律关系中心的基础判断。照此而言,做一下对比,我们可以说,上述的剩余权力的归属,也就决定了股东会还是董事会作为公司机构的核心地位。所以这种学说的说服力还是非常强的,可以较好的用于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中心的界定和判断。
但是也可以看到,按照公司立法的基本设计,公司治理中的绝大多数权力都是经过长久实践、反复梳理提炼并被类型化之后进行法定分配的,完全被立法遗漏、游离于公司法条和公司章程之外的公司事项已无许多,剩余权力并无太大的空间。而且,这些被遗漏的公司事项,无论从其与公司和股东利益关联与影响的程度还是就其实际发生的频度而言,一般都远逊于法律和章程明定的公司事项,对这些事项享有的剩余权力无论进行怎样的分配,都不太容易实质改变公司明定权力分配已经形成的治理格局,仅以少数无关紧要的剩余权力归董事会行使便认定为董事会中心主义似乎也有不妥。也就是说,以剩余权力归属来判断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和权力争夺,在立法和实践尚不完善的时候较有意义,但随着立法的严谨和科学化,以及实践经验的丰富,这一标准的意义在逐渐下降。当然在某些领域,例如公司重大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等问题上,无论是立法还是章程,都可能存在模糊不清的地带,这就会产生解释的问题,即解释权归属于股东会还是董事会。要注意的是,某些交易行为,从层级上看,可能并不属于法律或章程规定的重大事项,但数额可能相当可观,对公司可能产生重大影响,那么究竟是归入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范围内,还是第四十六条?
还有一个问题,剩余权力归属的观点,在特殊情形下的确具有界定公司治理中心的特殊意义,即当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处于主次不清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中心非常模糊时,剩余权力的追加极有可能打破既有的权力均衡,足以凸显或奠定 股东会或董事会的治理中心地位。因此,剩余权力的观点,在判断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和权力分配、争夺上,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的加强条件。
(未完待续)